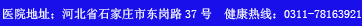一曲祠山文化的挽歌
2022/10/6 来源:不详治疗白癜风的中药有哪些 http://m.39.net/pf/a_4633653.html
徐宏杰
广德城西郊五里处的横山,西汉治水英雄张渤隐居于此死后葬于此,后世在此建庙宇以祀之,多年连绵不绝。唐天宝年间玄宗李隆基敕封横山为“祠山”,在此基础上形成的“祠山文化”源远流长。
老家东亭小镇,是张渤治水的重要的水利工地,保存有最丰富的“祠山大帝”张渤治水的遗址——圣渎(古运河遗址)、浴兵池(东亭湖)等,有名的挂鼓坛也近在咫尺。
上初中的时候,我听一位老先生说:年,从军队回乡的东亭人贺XX,为了造福乡里,实现自己为故乡发展教育的理想,将庙里的菩萨移走,利用祠山庙的建筑,创办了新式国民小学,使东亭老街周围的适龄儿童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。世事沧桑,办学几年之后,医院。祠山庙由教书育人的学校,医院,可以说,医院,“祠山庙”在老百姓心中都是至高无上的,“祠山大帝”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给东亭的老百姓带来恩泽。
时间久远,在这里办学、办医院的具体情况,后来人均知之不详,但是,正如上面提供消息的老先生所总结的那样:砸掉菩萨后利用庙宇办学是一种进步,医院是一种发展。无论从哪个角度说,张渤有知,一定会感到欣慰。
我在张渤祠山庙办学的“东亭中心完小”里接受了比较完整的小学教育,我是幸运的!
年,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,我回到家里的第二天,便去了一直记在心中的童年伊甸园——祠山庙——我念了6年书的“东亭中心完小”。
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,走出家门不远,加快步伐小跑起来。沿着古运河的遗址,一直向东半个多小时,小学的六年,每天往返两趟,熟悉的老街景色,尽管有了很大的变化,街道两边,基本上还是一方方似曾相识的老街人家——前面一个院子,后面一块园地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,母校到了,多少年心中挥之不去、生命的世外桃源,竟然是另外一番陌生景象,满眼是:鸭鹅遍地、羊芈猪突、鸡飞狗跳的热闹场面,不知成了谁家的“一亩三分地”。几栋难看、低劣的土墙平瓦搭建的建筑物,随心所欲、了无生机地躺在那里,取代了名冠华夏东南的祠山文化经典之一的璀璨明珠——祠山庙——东亭中心完小——我的母校!
母校不在了,彻底消失了!
我几乎屏住呼吸、头脑一片空白,呆在那里很长时间,莫名的伤感袭上心头,天哪!我心中圣洁的殿堂,不见了!祠山大帝巍峨的大殿,消失了!情急之中找人打听,多有语焉不详,敲开低矮的人家,见到花朵一般的孩子竟是那样茫然!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?”(贺知章《回乡偶书两首》)我想,眼前这满脸稚气的孩子是否知道他脚下这一块地方,曾经是东亭人精神血脉所系、流淌着祠山文化、浸润着张渤精神圣洁的土地?!
我心情复杂,情绪低落,在遗址上盘桓了许久。房前屋后掩埋在乱石泥土中依稀可见的一片片碎瓷瓦片,虽粉身碎骨,依然引起了我的注意,随手检出几片,擦去蒙在上面的污垢,露出了本来面目,瓷片洁白如玉,图案五彩缤纷。我虽不懂瓷器,焉知道这些碎片中有没有明成化斗彩、清雍正、乾隆官窑粉彩的身影?意外的是碎砖乱瓦中,发现几个基本完好的瓦当,上面的文字图案清晰可辨,虔诚地捡起几个置于囊中,后请教内行的人,瓦当上花纹就是常见的云头纹、饕餮纹,还有模糊的字迹。劫后余唾,一定是被毁掉的祠山庙宏伟建筑的吉光片羽。它们虽然失去往日的风采,仍然可以读出遗存的文化内涵。
被岁月侵蚀而蒙垢的瓷片、瓦当,作为“祠山文化”曾经的载体,无情地被弃置于荒凉之中!
正当我在废墟上盘桓的时候,这家大人回来了,听了孩子的话,马上到废墟上找到我,老远就大声喊我的小名,原来是很熟悉的张XX大叔。他老多了,而且左腿还留下了残疾,走路有点瘸。张大叔盛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喝茶,聊了很久。原来:几年前“祠山庙”所有建筑被毁,几棵参天大枫树也被连根挖掉,空出来一大片地方。这里是我们大队和东边的沙坝大队毗邻的地方,如果我们不来,他们就会捷足先登。张大叔兄弟4人,老宅拥挤,他家就搬到这里。
岁月不居。
脱胎于“祠山庙”的母校虽然灰飞烟灭,可是,留在我的记忆中的那几棵参天大树,60年代初,农村学校罕见的水磨青砖铺地的大礼堂(祠山庙大殿),以及礼堂两侧两个大天井中大荷缸、里面盛开莲花、色彩斑斓的金鱼;还有围绕在大殿四周几排精致的、青砖勾缝到顶的瓦房和其他许多漂亮的教学设施。雨雪天气我们在礼堂里上体育课,近似于今天的室内运动场——那时从没听说过的——让人想起来就觉得温暖。
礼堂里举行的各种活动,体育课上老师教的东西,早已丝毫记不得了,倒是在天井淋雨、玩水、赏荷花、喂金鱼的场面历历在目……
20世纪60年代,在一个经济落后,交通闭塞,文化荒芜的皖东南小镇有这样的学校,不能不说是故乡莘莘学子的幸运!
用老百姓因果轮回的眼光看,是“祠山大帝”的荫庇我们才有了这美好的校园,老街的子孙才得以在这里接受了比较好的人生启蒙教育。任何时候只要一想起母校,心里便充满了幸福和感激之情;就是到了满头白发、老眼昏花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今天,童年的美好时光总是不请自来地走进我的记忆中。
那一天我告别了张大叔,情绪低落地回到家里,接着,又情绪低落地回到工作中。
恢复高考后我上了大学,大学浩如烟海的资料,我开始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,尽我所能地要为消失的“祠山文化”找一点什么,留作回忆,以弥补内心的缺憾。矢志不移,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搜集、阅读了一些“祠山文化”的相关书籍和地方志,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,终于对原本在心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张渤及“祠山文化”有了一定的了解。
概括地说:以横山为中心的“祠山文化”,始于西汉末年,老百姓缅怀治水英雄张渤关爱民众,弥灾捍患,勇于献身的精神而顶礼膜拜,张渤的名字在民间广泛传颂。自唐至清先后有十八位帝王封禅张渤;明太祖曾统军过广德驻跸横山赋诗,有“天下英灵第一山”诗句,更是脍炙人口,在此基础上,形成了罕见的官民共祷的祭祀文化。继而张渤又被老百姓戴上了“广德王”、“祠山大帝”的桂冠。唐宋以降,张渤名扬皖南、苏南、浙北、赣北等地。
今天,有关张渤的人文历史神话传说,被文史专家认为,“是可与‘妈祖文化’相媲美、与佛道儒诸家贯通交融的历史文化奇迹。”
据明李得中等纂修《广德州志》(万历)记载:“祠山大帝,佐禹治水有功,后礼斗横山,其赛祷盛于广德州。”“离宫行宫遍江南”。自西汉神爵三年(公元前59年)广德横山建起了第一座祭祀张渤的神庙,又在城关东门修建了“娘娘庙”,之后华夏东南各地先后相继修建了数千座祠山庙,仅广德一地就建有70余座祠山大帝庙。“祠宇之盛,甲于东南”。
“东亭中心完小”的前身就是广德70余座祠山大帝庙之一。
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(公元—)古代中国地理志史《太平寰宇记》,记述了宋朝的疆域版图,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。有关“祠山庙”,本书这样记载:“祠山在县西五里,旧为横山,唐玄宗天宝年间(—)封为祠山”。迄今已有多年的历史。《历代神仙通鉴》载:天宝七年,全国遭受百年未遇大旱,唐玄宗立坛祭雨而应,敕封张渤为“水部员外郎”,建殿造庙仍觉不够,敕封横山为“祠山”,五代十国后晋南汉皇帝刘晨又册封张渤为“广德王”。其它有关民间史料还有这样的记载:横山之右有张真君庙,之左有龙潭王庙,张真君庙和龙潭王庙立于横山之左右,可见张渤地位之高。治水英雄张渤正式登上神坛。
民间尚有更细致的传说。
据说远古时代的氏族首领张渤是广德人。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,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,流传千古,家喻户晓,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精神寄托,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。同样,张渤治水的故事,在广德,在东亭广泛流传,洪水泛滥,浊浪滔天,人或为鱼鳖的远古时代,张渤就带领百姓,像大禹一样地奋战在江南和长江中下游。开山劈岭,疏浚河道,导引洪水,循江入海,变害为利,为大江南北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、百姓安宁、社会进步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治水在张渤家族有着深厚的传统。据记载,张渤的始祖张挥,有个孙子叫张秉,即张渤的父亲。张秉即跟随大禹治水几十年,走遍神州大地,造福于民。张秉为人忠厚,又能吃苦耐劳,深得大禹信赖。张秉治水之功感动上苍,喜得贵子,取名渤,寄希望于他为民造福,一生治水。张渤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,为制服水害奋斗一生。
今天的东亭老街,张渤治水遗址,保存最丰富、最完整。
最为有名的是,张渤为了解决开挖河道的大军沐浴而挖掘了“浴兵池”,就是今天亩碧波荡漾的“东亭湖”。由于选址合理,既解决了开河大军生活需要,蓄水之后,遇到干旱的年景还可以灌溉湖下数千亩农田,是一个惠及子孙的水利工程。湖下这一片辽阔肥沃的土地,平畴延展,得湖水的浇灌可谓是旱涝保收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东亭人。
我对这一泓碧水感受深切。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,上大学之前,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,随父辈在这一片土地上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辛勤耕耘,抛洒汗水,深得湖水之利,记忆中的“浴兵池”,不仅是张渤给后人留下的一处文化遗迹,更给择湖而住的东亭老街人提供了许多便利。
同样,还有在东亭人心中地位神圣的“拖锹冲”和“饭石山”。
成书于清康熙十二年()《祠山志》记载:东亭的“拖锹冲”、“饭石山”,都是张渤治水开凿“圣渎运河”留下的遗迹。这两处浸润着“祠山文化”的遗存,位于东亭老街东亭湖边,在我家边上,小时候我经常是一天造访若干次。我家对门刘大伯家的后门紧挨着拖锹冲。我家后门几十步就是东亭湖,湖的那一边即是饭石山。“圣渎”和饭石山,咫尺之遥,一南一北,隔湖相望。
先说说饭石山。
饭石山位于东亭湖北边,山不高,紧挨着湖,湖水日夜拍打着山脚。我们从小就知道,湖边饭石山上的石头很特别,赭色的底色布满了白点如同满天的繁星。不知道这是什么石头,只是觉得很好看,常弄一小块在手里把玩。后来曾多次见到地质队来此勘探,我们才知道这是他们在找寻麦饭石矿,饭石山大概得名于此。
也许是对英雄的膜拜,加上民间传说的影响,史书上对饭石山的记载蒙上了神话色彩。《万历志》载:“张真君饭时余粒,化为细石,如饭粒然。”这里的张真君就是张渤。我们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:相传太上老君有一次东游海上仙山瀛洲,同行的有:玉皇大帝,王母娘娘,元始天尊,太上道君,东华道君,太乙真人,等等。途中用膳,饭后余粒撒到东(亭)湖,饭石山由此得名。“张真君”在老街流传的故事里又演变成“太上老君”或“太上道君”等众位神仙。这样的传说为什么能广泛流传?如唐代刘禹锡所说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应该是我朴素的乡亲们对饭石山另一种景仰。
再说圣渎运河。
张渤开凿的“圣渎”干涸后,就成为当地老百姓的良田,据说,这是张渤治水遗迹保存最为完好的部分,在皖浙交界的丘陵间逶迤起伏,不过已经不太能看不出当年水利工程的规模了。
从“东亭中心完小”身旁经过已经干涸的“圣渎”,成了古运河遗址,成了水稻田。因地势低洼,当地人称之为“冲田”,不知道确切的面积。只记得人民公社时期,西边的11队和东边1队,每个队都有2到3坵不等。最东边毗邻沙坝大队,再往东就是东升大队(施家境),再往东就是浙江安吉的高禹、里港、外港、鄣吴村。冲田因地势低洼,积水难去,水是不愁的。插秧没什么,割稻的日子往往在泥泞中拼搏,半天,全队男女老少齐上阵,收工的时候,大伙全成了泥人,横身上下只见白色的牙齿和转动的眼珠。好处是冲田管理比较简单,大概是土质的缘由不生杂草,插秧之后只需几次用长长的弯把耘刀把田里的水搅浑就行了,产量不低且旱涝保收。
有人或许会问:在皖浙之间开挖圣渎意义何在?
张渤开挖“圣渎”的目的,《横山志》记载得简明扼要:旨在自浙江长兴贯通广德,途径浙江安吉县的梅溪镇、高禹镇,顺着山势至广德东亭的施家境、拖锹冲、打鼓垱、兰塘连接城关的无量溪,流至桐汭河,再流经郎川河,连通郎溪县、广德县之间的南漪湖直达长江,开辟了一条自著名的杭嘉湖平原,行水路至长江的内河航运水系。
尽管蓝图宏伟,壮志凌云,因社会动荡,财力拮据,英雄有志,岁月无情,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(杜甫《蜀相》),张渤死后,从而导致群龙无首,后继无人,这一项伟大的工程也就半途而废。前几年回老家看到有关部门已在“拖锹冲”路边挂上了“古运河遗址”的牌子,运河变良田,正应了“沧海桑田”那句老话,但是,张渤治水的精神是不老的。
最后说说祠山庙。
张渤祠山庙建筑群,左边依傍着“拖锹冲”——“圣渎”,右前方隔着“浴兵池”——东亭湖和饭石山隔湖相望。
“浴兵池”和“圣渎”运河簇拥着祠山庙,像卫兵一样护卫着张渤圣殿——祠山庙,临湖拔地而起的饭石山拱卫在不远处,形成了紧凑的“祠山文化”的格局,可见当年修庙人匠心独运。
上学的时候,紧挨着湖水和圣渎运河,掩映着校园的参天古木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8棵高大的枫香树张开巨大的枝桠在空中为“祠山庙”连成了绿色的屏障。这些树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,树高大约20几米,胸径大概2—3米,树的主干差不多3个人才能合抱。
最让人称奇的是一棵耸立在古运河遗址“拖锹冲”水田边,紧挨着我们学校的一棵高大的枫香树。我们上课的时候,坐在教室就能清楚地看到它。树身约3到4米高处有一大片黑色的疤痕。据老人们讲,那是很久以前,一条巨大的蟒蛇精隐居在大殿的阁楼中,每逢刮风下雨,从窗口探出身来在湖中喝水,有时在大殿另一边缠在这棵树上,意欲加害路人。天上雷公为正义除恶,一声巨响,劈死了蛇精,树身也被雷火烧掉一大片,深深地凹进去,树身这一节只剩下薄薄的一片。雷火大概烧在上个世纪初,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,我们上小学的时候,高大的枫香树怀抱着巨大的伤疤,依然郁郁葱葱,浓密的枝叶一如既往地在我们教室上空搏击风雨。
岁月悠悠,历史对张渤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在广德和广德周边地区,人们怀念、祭祀张渤一生开河治水、奉献自己、造福人类的无量功德,逐渐形成了祠山寺、祠山庙会、祠山民间文艺、祠山神话传说等民间传统文化,以及大量的文献资料:《祠山志》、《祠山小志》、《祠山事要》、《祠山事要指掌集》等。
据元末明初文学家、史学家陶宗仪所辑文言大丛书《说郛》一书中相关篇目《三柳轩杂识》、《祠山神事要》、《能改斋漫录》《留青日扎》等,对张渤在广德记载得十分具体,有名的挂鼓坛的传说生动传神:“(渤)……二月八日生,本前汉吴兴郡乌程人,始于本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,役阴兵导通流,欲抵广德县,故东自长兴、荆溪,疏凿河流,欲达宣、广、郎南漪湖,开河贯通形成内河水网,以抗洪防暑,行船通商,造福人民。”张渤化身为豨从阴兵,后为夫人所见,其工遂辍。东亭附近的“挂鼓坛”的典故说的就是这件事。张渤在东亭化大豨开挖圣渎,和传说中大禹化熊凿轩辕关,如出一辙,感动了很多人。清人赵绍祖有诗记之曰:“轶事同神禹,心疑敢腹诽。”(《谒横山庙》)细节虽有出入,对英雄的礼赞是一样的。
还有一种说法:张渤遁于广德县城西北5里横山之巅,修炼得道,人称“禹后第一人”。张渤死后葬于横山顶,当地人思念他,在横山修建张公祠即祠山庙于横山西南隅,夫人亦至县东二里而化,时人亦立为“娘娘庙”,与祠山庙遥相呼应。江南以及苏南、皖南、浙江、赣北等地各州县乡镇纷纷仿效,修建了大量的祠山庙、娘娘庙。广德横山的祠山庙被推崇为“祠山祖庭”,并称“天下第一香火”,从此祠山寺庙的规模越来越大,香火越来越旺盛,从而使横山和“祠山庙”的繁荣达到了鼎盛。
祠山文化发扬光大的同时,历代文人墨客也纷纷投来